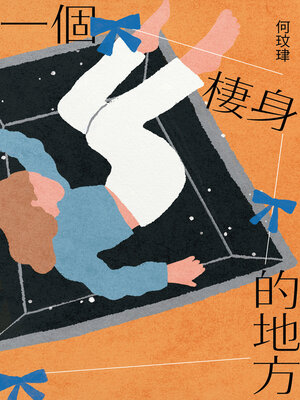Sign up to save your library
With an OverDrive account, you can save your favorite libraries for at-a-glance information about availability. Find out more about OverDrive accounts.
Find this title in Libby, the library reading app by OverDrive.



Search for a digital library with this title
Title found at these libraries:
| Library Name | Distance |
|---|---|
| Loading... |
獲台灣文學金典獎的新世代作家何玟珒以家族為底本的書寫,描述遷移、逃離、暫住或長居的那些住所,母親塑養孩子的身體髮膚產生的變化,以及家族在身體與語言的權力場域中展開的角力。
本書獲國藝會創作補助
作家 馬翊航
作家 張馨潔
作家 盛浩偉
作家 陳栢青
中興大學台文所副教授 陳國偉
作家 劉梓潔
作家 蔣亞妮
作家 顏訥
買房力推
年紀輕輕就買房,是一件冒險的事嗎?徒手接下家族長輩有形與無形的記憶檔案,是意念還是因果?如若書中那大樓的牆壁太薄、實聲與幻聽四竄,這本散文集的牆壁也是薄的——皮膚那種。經由調度「人稱」寫作,玟珒也調度生命種種複雜感受的距離。比起創傷、哀愁等詞彙,也許她文中提到的、按摩時「身體的結」更為傳神。一篇篇關於居所、身體、語言、家族的點按,看似不特別新鮮的主題,她卻有如揉散、燒炙、針入的種種解方。韓江的〈九章〉(收於《植物妻子》)裡說「人身上最能代表其精神狀態的部位是什麼,那時我的回答是肩。」按摩是不會治好一種病的,但它帶來接觸,帶來轉移,甚至關注一些奇異的角度、未曾使用過的肌肉。閱讀《一個棲身的地方》,也可以是按摩。感受到的不是安居樂業之法門,而是久存的氣結。我的、家庭的、社會的。因為棲身本就是一件危機四伏的事。——作家馬翊航
一本向外同時也向內質問的散文書寫,質問式的自白展現何玟珒在書寫已先早在自我的形構上鍛鍊出強韌的質地,然而,既能聰敏的幾近看透親緣糾葛,為何悲傷仍然如影隨形?這是我眼中這本散文所提出的核心命題。那麼只有一次、再次的撬開自身背景中的磚瓦,看見縫隙中在無光潮濕之處的蟲蠅,以及不知何時被蛀蝕的結構,鑽探與透析之中,書寫糾結的緣起與不可解,情緒上的敘述節制減省,只告訴你她需要在夜間散步才能平靜,服藥才能安眠,將主力放在分析與辯證中,以一種直面命運的坦然與爽俐,展現出新生代散文書寫上另一種亮麗的切面!——作家張馨潔
雖說「話到滄桑語始工」,然而生命不幸的經驗,之於散文未必是幸事。只因散文要求書寫者直面這災禍核心,片刻無法閃躲,然而卻也因此,一不小心就會淪為苦難的競技場,彷彿誰傷得愈深、痛得愈重,誰就能享有文學至高的光榮——但不是這樣的。直面才能看清,看清是為度化——對,不是慈悲原諒救贖或放下,而彷彿更接近於度化——那才應該是讀/寫散文的意義。
在《一個棲身的地方》中,何玟珒以銳利卻淡然之眼,看透自己生命經驗裡的傷與痛,也看透了血緣親近之人的艱難處境,並以冷徹不煽情的文字娓娓道來。可縱然書中寫盡成噸的苦難,光是這篇與書名同的〈一個棲身的地方〉,就已超脫真實與虛構的層次,達至度化的境界。這是足堪一名作者引以為傲之作。——盛浩偉(作家)
上個世紀最大的驚嘆號給吳爾芙,她說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間。何玟珒只添一個S,把女人變成複數,就把驚嘆號變成問號。所以一屋子女人們,誰來分配房間?何玟珒寫家屋其實是寫家,母女是冤家,寫城市遊牧其實是寫生存方式,那只是住,又該怎麼活?她的散文最講樓地板面積,坪坪討價還價,非常之不講情面,太敢講,半點不饒過人。她的文字是這時代的良心容積率,不摻水,都是實。就怕太實了,用筆尖逼得那麼緊,先逼自己,才能逼別人,沒半點陰影殘留,天寬地闊,偏與內在的自我四目相對,無處可避。拎包入住,不如帶本何玟珒,散文裡不缺狠人,但沒看過何玟珒這麼狠的。她能對自己狠。我們讀著讀著都因此乾淨了起來。近乎空。一種斷捨離。——陳栢青(作家)
在讀《一個棲身的地方》時,那些反覆被書寫開啟的不同空間,比如老家、舊房間與小套房,總讓我想起巴舍拉說的:「我們的家屋就是我們的人世一隅。許多人都說過,家屋就是我們的第一個宇宙(Cosmos),而且完全符合宇宙這個詞的各種意義。」每個宇宙,都會成為召喚者的記憶負片,幸與不幸,同時存在;何玟珒沖洗著這份私密感,反覆將某些場景變成鎖、變成匣、變成自己。正負一體,翻轉出了無數門,種種以「懷恨」或「遺恨」命名的書寫之門,或許門後是命名者尚未通往的地方,那裡的人半開半闔,那裡的人疑愛疑恨。——蔣亞妮(作家)
「既然如此,妳又為什麼要寫?」在《一個棲身的地方》中,何玟珒頻繁地使用第二人稱,將自己與創傷經驗砸出來的巨大坑洞,隔出又遠又近的觀測距離。她也用第二人稱,把母親從那個暗鬱坑洞前推遠,又悄悄拉近。正是在這個用書寫撐出來的微妙觀測距離中,她得以警醒地一再詰問:「既然如此,我為什麼要寫?」這個其實艱難的提問,來自散文寫作者對自己必要之殘酷。因此,我珍惜小說家何玟珒的散文。在她的散文裡,有人走身心的夜路,又狹路相逢。有人走在物理與心理空間的畸零地,用隱匿劃定界線。無法隱匿的是,母親用養護與苛責奪取女兒的身體。女兒用身心疾患,用知識,用語言,搶回自己的輪廓。一如文中母親學習日語時,因肌肉僵化而難以準確發音,《一個棲身的地方》的家族書寫,每一次發音,都是一次肉痛。至此才發現,何玟珒用第二人稱重寫母親,是一種多不容易的讓渡。——顏訥(作家)
家屋就是人世一隅
敲開裸露自我的屋瓦,掀揭潮濕隙縫的蟲居,直面來自身體與空間的傷痛,
讀著何玟珒的文字,在糾結的親緣間尋找化解,身心獲得近乎斷捨離的療癒。
榮獲台灣文學金典獎的新世代作家何玟珒,繼備受矚目的小說集《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後,首度出版散文集《一個棲身的地方》,描述遷移、逃離、暫住或長居的那些住所,書寫家族間的愛恨交織。
全書分為四輯,「空間書」記錄作者所待過的房間,並援引建築史發展脈絡來闡述空間產生的意義。同名篇章〈一個棲身的地方〉,寫母女三人不停地遷居,以及儲物症的母親如何安排女兒的房間,用女兒來寄居她的匱乏,把丟掉可惜的舊衣置放在女兒的衣櫥。「身體書」將個人的身體視為一個權力場域,透過掠龍的〈傳導痛〉和做臉的〈面子問題〉,觀察母親如何塑養孩子的體膚,以及親子掌控權拉扯的微小角力。「舌頭書」藉由學習語言的歷程,思考自己在使用語言的背後所認同的我父(本省第二代)與我母(外省第二代)之歷史,微觀舌上之語,映照經歷兩種不同脈絡的〈少女政治史〉。「家族書」透過〈父女〉與祖父往生的〈告別式〉,講述個人對原生家庭接近與斷捨離的家族史。
身體不光是被動盛裝的容器,銘刻學習的經驗、遭受的苦痛與生活的因果;身體作為一個棲身的地方,亦主動以舌頭五感和外在的環境、周遭的人們互動。何玟珒敲開裸露自我的屋瓦,掀揭潮濕隙縫的蟲居,直面她幽微的、來自身體與空間的、難以言說卻迴避不了的種種傷痛。她在不成眠的夜間散步尋求平靜,在糾結的親緣間尋找化解,遊走於感性抒情與理性論辯的敘事結構中,一筆一畫專注地鑽切和剖面自己,試圖把所有長滿蟲蝨的衣服與居所,光雕成華美的生命的殿堂。